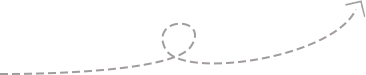安介生: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中山西的区位价值
访问量:1067
作者简介: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等。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与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编委、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年入选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励计划,2013年荣获首届中华晋商关公奖“中华晋商崛起20年十大研究专家”称号。撰写与编著《山西移民史》《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大迁徙》《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就高度评价了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实际上为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山西研究热”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二十余年来,山西地方史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吸引了中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在这种状况下,夯实这一领域的基础,扩展这一研究的外延与内涵,成为当务之急。笔者大力倡议将“小晋学”扩展为“大晋学”,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与意愿。而从“小晋学”扩展为“大晋学”,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飞跃,需要更多的理论探讨与摸索。在本文中,笔者在总结二十年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中山西的区位价值进行一个更清晰、更系统的阐发。抛砖引玉,以就正于高明。
一、历史时期山西区域整合与整体区位价值之评述
(一)山西在中国历史地理上的特殊区位价值
历史时期最早高度评价山西地区的区位价值的著名学者,当推金元时期的郝经。他曾明确指出:
夫河东,表里山河,形胜之区,控引夷夏,瞰临中原,古称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党号称天下之脊。故尧、舜、禹三圣,更帝迭王,互为都邑,以固鼎命,以临诸侯,为至治之极。降及叔世,五伯迭兴,晋独为诸侯盟主,百有余年。汉晋以来,自刘元海而下,李唐、后唐、晋、刘汉,皆由此以立国,金源氏(即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故河东者,九州之冠也。
历史区位价值的评断,不仅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在于现在环境的刺激,郝经之论证实了这一点。郝经之所以能够超迈前人,高度评价河东的区位价值,一则出于乡土关系,他本人是生长于山西的学者,对于乡土的关切与思考自然多于其他学者;二则河东地区的区位价值在辽金宋夏时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充分利用河东的区位价值为王朝政治服务,也正是郝经上言的主要动机。
当然,与古代学者主要为王朝政治服务的立论宗旨不同,今天的学者们完全可以从更开阔的视野与长期的时间跨度,以及从政治演变史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与思考区位价值问题。就晋学研究而言,宏观上的思考与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时期,影响中国历史演变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然而政治演变与民族发展,无疑是两种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下面,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从整体上对于山西的区位价值作一个简要总结。
1.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与华夏族国家成长之典范
先秦时期民族的发展往往以“国”、“邦”等外在政治形式表现出来,族群的发展伴随地域范围的变化。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总结刘向、朱赣等人的著述后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古有分土,亡(同无)分民。”颜师古释之云:“有分土者,谓立封疆也。无分民者,谓通往来不常厥居也。”从迁徙无定,不常厥居,到分立疆場,封邦建国,均为民族与国家发展与壮大的标志性的阶段特征,而择地定居,分立疆場,意谓着地域区位价值认知及利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先秦时期,对于今天山西地区区位价值的认知,是与晋国的发展分不开的。
根据现代学者的总结,邦国林立,争霸称雄是先秦时代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而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可称为“四大王国”角逐争雄的时代。按其地理方位,西有秦国,北有晋国,南有楚国,东有齐国。如《史记·周本纪》载称:“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上述著名王国逐渐强盛的时代,就其族属而言,齐、晋为华夏,秦、楚则为戎蛮。
先秦时期晋国的发展史是华夏民族与国家成长的一个缩影:就疆域发展而言,从河东一隅“百里之地”崛起,最终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来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国之领土几乎覆盖了北半部中国,在“战国七雄”中占了三家。而就族群发展而言,晋国是在周边四裔族的包围下发展起来的。“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国的拓展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性,日益扩展的疆土对于晋国的治理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如在晋献公晚期,当时人对于晋国疆域管理发出了忧心忡忡的感叹:“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晋国的发展依然势不可挡。
还必须看到,晋国对于东周王室的存续起到了重要支撑,这已成为学术界共识。如晋国为秦国的强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力地阻碍了秦国的东扩。清代学者顾祖禹指出:“(春秋时期)当是时,秦日以强,缪、康、桓、景诸君,其材足以争雄于中国,而成周无恙,东诸侯之属不遂罹秦祸者,不可谓非晋之大有造于天下矣。”又顾栋高在《晋疆域论》中对晋国的建设成就备加推重:“……盖天下之无王,自晋始。及势既强大,乃复勤王,以求诸侯,周室之不亡,复于晋重有赖焉……天下扼塞巩固之区,无不为晋有,然后以守则固,以攻则胜,拥卫天子,鞭笞列国,周室藉以绵延者二百年……”
2. 地处农牧交错带——连接农耕民族与牧业民族的桥梁与纽带
山西的自然地理形态是南北长,东西狭,北部地区正处于中国农牧业交错带,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山西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占有极为独特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山西北部地区长期作为统一王朝的北部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城一线自战国后期以来,已为中原各国北部边界,秦汉建立以来,这一分界线得到前所未有地巩固与认定。“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山西北部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北边政权南侵的最重要据点之一,也是北方民族政权南侵攻掠的主要地域,史书上的相关记载不胜枚举。
其次,秦汉以来,长城一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是南北政权的疆域分界,也是民族区域的分界线。南北民族往来最为频繁的区域就在山西中北部地区。因此,山西中北部地区在很早的时候在地域文化上显示出过渡性与模糊性的特征。
其三,特殊的地理形态使山西成为北方民族南迁的“孔道”或“首选之地”。如在东汉初期,南、北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即迁入东汉缘边七郡之中,这七郡地域涉及今天河北、内蒙古、山西等省区。而后来南匈奴则较全面地迁入了山西、陕西交界地区,从“塞外之虏”而演变为“并州之胡”,在山西 西部的长期定居生活,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后来出现的“稽胡”或“山胡”族群正是南迁匈奴族为核心的民族混合体。
绵延的长城涉及南北区域非常广大,而为何选择山西地区作为南迁之首先地呢?应该说,这肯定不是随兴所之的或然之举,而是有经过全面思虑之后的选择。如北魏名臣崔浩等人曾力阻明元帝迁都于邺城,他着重指出:
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指代都平城),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䇿也。
崔浩所言精辟地总结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十分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何北方民族选择雁北地区作为根基之地,并将山西地区作为南下孔道的真实历史地理形势。
3. 支撑中原王朝延续与发展的“金三角地带”
山西地区在分裂时代的重要地位,已为学者们所反复强调,但在统一时期的政治地理作用似乎并没有被较深入的讨论过。笔者以为:历史时期统一王朝之下,山西同样具有并发挥了非凡的区位价值优势。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地理区位的另外一大特征,则是深入中原腹地。从秦汉到隋唐,甚至在元明之前,长安——洛阳一线在大部分时段都处于中国政治中心区,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中轴地带”。首都的选择都在这一线移动。《汉书·地理志》称:“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在这种政治地理形势之下,纵贯南北的山西深入“京畿”之地。在这种客观状况下,无论是定都长安的西汉时期,还是定都洛阳时的东汉及西晋,山西西南部河东郡都为“司隶校尉部”或“司州”(相当于后世的畿辅之区)组成部分,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而晋朝之得名,源自司马懿封国于晋国,而在西晋时期,河东郡与平阳郡(由河东郡分出)同样是司州的组成部分。
山西地区的政治区位优势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州的北都,河中府的中都,与上京、东都构成了唐代疆域中的“金三角”核心区。唐代的北都太原府、中都河中府分别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构成了大、小两个“金三角地带”,而“大金三角地带”又包含了“小金三角地带”,正是唐代政治地理版图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的“枢纽区”。河东地区在唐代政治及文化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奠定。“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其政治核心区——“金三角地带”也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面临瓦解崩溃的危险,而作为“金三角地带”最稳固的一角,河东地区的区位优势与价值更为凸现,成为维系唐朝后期政治延续的重要支柱。
(二)山西区域之整合历程
任何一个区域名称都有其时段性,今天“山西”作为一个完整区域的整合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在历史时期今天的山西省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但是,山西地区的最终整合带有很大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自然地理形势与人文特点上揭示这种合理性与必然性,对于研究山西地区的整合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在自然地貌特征上,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山西方舆纪要序》中称赞山西的自然地势“最为完固”,可以说,山西地区边缘地带在自然地貌上构成了一个封闭上很强的地理单元,即左有太行山,右有黄河及吕梁山,北有长城,南有黄河等,与周边地区存在十分明确的地理界线。
但是,自然地理形势的认识与利用,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谓地理整合过程,实际上是地域观念认识的整合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对于一些较为宏观的地域观念的认识及总结来表现出来。山西地区的整合过程主要以通过分析三个核心词汇来表现出来的。这三个整合词汇便是并州、河东与山西。
“并州”一词最早出于《周礼·职方》:“正北曰职方。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先秦时期的并州是理想化的产物,是十二州之一,并非最早的“《禹贡》九州”之一,而是由九州中的冀州分划出来的。北魏孝文帝在主张南迁洛阳之时,提出的一项理由是平城所在的雁北(云中、恒州)地区在“九州之外”。
并州进入正式政区始于西汉武帝时期,为当时设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其下领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六郡,到东汉时又增领西河、五原、朔方、上郡等,其所辖地域相当广袤,包括今天山西中北部以及河北、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狼山、阴山以南地区,但并不包括今天山西晋西南(河东郡)地区。历史时期州制的发展趋势是从“大州”时代逐渐演变为“小州”时代。在当时的管理条件下,在面积过于广袤的政区实现有效治理,是很不现实的,在实际上其管理效能也是十分有限的。在南北朝政区淆乱之后,并州之名往往成为太原府或太原郡的代名词。
与“并州”一词由大而小的变迁过程不同,“河东”却是有一个明显的由小而大的扩展。河东郡为秦朝所置,因地毗关中地区,秦汉时代,河东郡一直被划入京畿的范围之内。唐代设置有贞观十道及开元十五道,河东道名列其中,这也真正开始了以河东统领今天山西省这片区域的历史。而道制设置之始,与最初的州制相仿,均非正式政区,而是监察区。唐朝中后期,节度使专权,今天的山西地区分为三个节度使,即河中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以及眧义军节度使,其各自管辖地域已与河东道大有不同。北宋设置河东路,但是限于整体疆域形势,其所辖地区北并不包括雁北地区(辽朝西京道),南不包括河中府之地。而金朝在今天的山西地区不仅设立了西京路,还设置了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同样将今天山西省的地域分成了三个部分。时至元代,今天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均归入中书省的管辖,而所设置的“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将山西省的几个部分整合在了一起。
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三一“河东山西”条中指明:“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然而,通过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与形势变迁,笔者认为:历史文献中“河东”与“山西”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地域名称,以往学者没有能够发掘出“山西”之名演变的真实轨迹。笔者以为:以辽金时期为界限,文献中的“山西”概念内涵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内涵可以称得上传统的“山西”观念,指“陕西华山或崤山以西”地区。辽金时期开始,一种全新的“山西”概念出现了。契丹人习惯以燕山及太行山作为确定方位的座标,将汉人居留的今山西雁北地区称为“山西五州”。金代在此地区设“山西路”,山西之名通行于王朝政令之中。辽金时期的“山西五州”及“山西路”正是元朝“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设置的依据,为“山西”转化为政区名称的真正渊源。
二、历史时期山西境内各亚区之区位价值管窥
在山西地区漫长的整合过程中,其总体价值的体现往往是较为抽象的,较为曲折的:与之相反,历史时期山西地区所属各个亚区的表现却是相当活动与突出的,在一定程度度上可以说,山西在历史时期的区位价值更多的是通过这些亚区所体现出现的。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中有相当突出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山西地区所属重要的亚区有:河东地区、晋东南地区、晋中地区、吕梁地区、雁北地区和忻代地区。下面笔者分别选择典型时段简要说明山西地区各亚区在中国前近代历史中特殊的区位价值。
(一)河东(晋西南)地区之区位价值
山西地区地上文物之繁庶,以及在远古历史中的价值与地位,早已为古今学者们所称道。这尤以晋南(晋西南)考古成果为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东地也。”这是古代学者们关于远古都城变迁较为一致的结论。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根据考古资料,对于晋南(实为晋西南)在上古文化时代的重要地位推崇备至:“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从中原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到(晋南)陶寺遗址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至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即谓远古邦国时代最初聚集之中心,就在今天山西西南部地区。
从先秦直到秦汉以后,河东地区作为“三河”之一,长期居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及文化核心区域。《史记·货殖列传》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逐鹿中原,问鼎中国,而“三河”正是“天下”(“中国”、中原)之核心区。在这里,王都集中以及建国时间漫长,都是古人评价区位价值的重要指标。
霍山以南的河东地区是晋国的核心区,也是晋国进一步拓展的基地。又如河东郡最初为秦朝所置,长期隶属于司隶校尉部及司州,为中原王朝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区,这种政治地理地位直到元明以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唐朝又是河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突出标志便是河中府中都与河中节度使的设置。在唐朝后期,长安地区受到吐蕃军事威胁之下,于是元载等人甚至建议迁都于河中府,虽然建设最终并没有采纳,但学者认为其建议“尽当时利害”。这也都充分证明了河中府地区的重要地位。
(二)上党(晋东南)地区之区位价值
晋东南地区所在晋东南高原(或称沁潞高原)位于山西高原的东部边缘、太行山西南端,地势较高,海拔800——1200米。太行山势西部平缓而东坡陡峭,与黄淮海平原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落差。这种特殊的地势条件对于晋东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正如前引郝经《河东罪言》所云,在古文献中所谓“天下之脊”所指地域不一,而太行山以及上党地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上党地区紧毗中原之要区,然地势高耸,居高临下之态自然很早就得到古人的高度关注。“上党初置郡时,奄有潞、泽、沁、辽之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今河南淇县)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东亦环趾而处于山之外也,乃其势东南絶险,一夫当关,万军难越,西北绝要,我去则易,彼来则难,夫非最胜之地哉?!”
先秦时期晋东南地区曾有一个很古老的邦国——黎国,后来为赤狄潞子之国所攻灭。地处晋东南地区的赤狄潞氏之国有着相当完备的国家组织,且疆域广大。如清代学者顾栋高着重指出:“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又“晋之灭潞也,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曲梁为今广平府永年县(治今河北永年县),盖反出其东而转攻之,则即一潞氏而疆域之广亘千有余里。”即谓潞氏之国是当时最强大的赤狄国家,疆域横跨今山西、河北两省,因而成为当时赤狄族群之盟主。“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在晋国扩张过程中,潞氏之国曾为其头号强敌。晋国与潞氏国之战,也是晋国扩展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十六国时期,前秦攻灭了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大批鲜卑被强迁入关中地区。在“淝水之战”之后,盘踞在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乘机反叛,在残酷的厮杀之后,幸存下来的鲜卑部众力求返回关东地区,而其中慕容永所率领的一支鲜卑部众进居晋东南地区,在长子自立称帝,史称“西燕”。
唐朝中期以后,驻节于泽潞地区的昭义军节度使,因其地处唐朝京畿与河北藩镇之间而成为左右唐朝王朝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重要的区位价值已为当时人所肯定,如唐人杜牧在《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一文中指出:“……伏以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悦名曰腹中之眼。带甲十万,籍土五州……”当然,无论是“天下之脊”,还是“腹中之眼”,均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如果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那么这样的评价就会给人以夸大不实之感。
(三)晋中地区之区位价值
今天山西中部地区即晋中,为古代晋阳、太原郡及并州等政区所在地。对于晋中地区的早期发展史,唐人李吉甫等人所撰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曾进行较详细的考订,认为晋国大夫荀吴击败狄人之地“大卤”,正是太原晋阳县之地,进而指出:“按晋,太原、大卤、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将这样六个古地名合而为一,充分证明了晋中地区上古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在晋国兴起之时,广大的晋中地区确实为戎狄人的居留之地。公元前541年,晋国军队与晋中地区的进行了一场空前大战。《左传》昭公元年载云:“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大败之。”晋国在这场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在晋中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进而控制了整个汾水流域。
晋阳太原府为唐王朝创兴之地,天授元年建为北都,天宝元年更改为北京。政治地位达到一个高峰,同时又为河东道驻理之地。“又于边境置节度使,以式遏四夷,河东最为天下雄镇。”可以说,河东镇可谓唐王朝存亡攸关最重要的北方重镇。在安史之乱后,河东节度使忠诚于中央朝廷,力挽唐王朝之颓势,居功不小。顾祖禹曾精辟地总结道:“及安史之乱,匡济之功,多出河东。”
与关中地区相仿,以太原为核心的晋中地区也以“四塞之地”著称,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为政治割据者们所青睐,先后成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等多个割据政权的政治核心地。
(四)吕梁地区之区位价值
吕梁地区地处山西西部吕梁山脉与黄河之间的晋西高原,在地貌上山脉丘陵居多,与雁北地区同属农业生产条件较为恶劣的区域,由于历史时期汉族人口较为稀少,因此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聚居的理想区域。
吕梁地区在两汉时属于西河郡,“西河”之名,本义谓其初置于黄河之西,而两汉时期所置西河郡则横跨黄河,面积相当广大,包括今天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部,远远超出今天山西吕梁地区的地域范围。在《汉书·地理志》中,西河郡与安定、北地、上郡等一道同属于一个西北边塞风俗区,“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西河郡并未以河为界,因此黄河中游河道并没有成为风俗文化区以及东西两岸交往的阻隔。
东汉初年,南北匈奴分裂后,西河郡并不是安置南迁匈奴部众的“沿边七郡”之一,但是,这并不影响匈奴部众逐渐向这一区域汇聚,进而迫使东汉后期及三国时期西河郡治所的内迁,先后从平定(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迁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市)与兹氏(今山西汾阳市),治所的迁徙意味着辖地的放弃。最终,“十六国时代”的首作俑者——刘渊汉赵国首先创立于离石,这正是匈奴南迁以及长其聚居这一地区的结果。北朝时期,西河地区为“山胡”或“稽胡”聚集之地。“山胡”或“稽胡”为南匈奴后裔与其他北方部族的混合体,强盛的“山胡”族群成为北朝后期影响北方政治变迁的强大力量。清代学者顾祖禹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东汉之季,西河尤为多事,迨于刘渊发难,中原陆沈,祸乱之征,未始不自西河始也。”笔者以为:如果离开民族迁徙的背景,我们是根本无法理解导致当时形势风云突变的真正原因。
辽与北宋对峙时代,雁北地区已划归辽国,山西中西部地区承担了来自“西(夏)、北(辽)二边”的压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尤其是山西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辽朝与西夏的夹击之下。北宋在山西西北部设置有石州、隰州、岚州、麟州、丰州、宪州、府州以及火山军、保德军、晋宁军、岢岚军等,政区及军管区设置之密、等级之高,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其中丰州、府州、麟州、晋宁军等因地处黄河之西,属于北宋关键性的战略前沿,北宋与西夏在此长期交相攻守,争夺十分激烈。
(五)雁北及忻代地区之区位价值
就其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这一地区很早便是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交错地带,即同时具备了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活动的自然条件与基础,但是,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十分优越,交错性与过渡性特征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北朝时期、辽金时期以及明代前中期,山西北部地区在政治与军事史上都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家分晋后,赵国北向发展,占据雁北与忻代地区,华夏汉族第一次全面控制这一地区,而到东汉初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部众进入雁北地区,到三国西晋时期,忻代以北地区并弃之,即中原王朝已放弃了这一地区,而拓跋鲜卑正是在这一地区壮大起来,以恒代(雁北)地区为基地,建立起强盛的北魏(或称后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是雁北地区区位优势得以发展与利用的一大高峰。
南北朝后期以及隋唐时期,塞北又成为南北民族激烈争夺之地,战事频繁,盛唐时期,大量塞北民族南迁,雁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安置北来降众的区域。唐后期及五代时期,契丹人崛起,石晋时期被迫割让“燕云十六州”,于是山西雁北地区成为辽朝“西京道”之地,大同也成为辽代“五京”之一,成为其国防体系之的“西大门”。金朝继承了辽朝的“五京制度”,大同府所在之地隶属于西京路,同样是金朝西边重镇,西京留守司即驻守于大同。
明代前中期,重返塞北草原的蒙古人频繁侵袭北方边界地区,山西北部首当其冲,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频繁的侵袭给山西百姓带来了惨重的伤害。为抵御北方蒙古人的侵袭,明朝建筑了规模浩大的北方防御体系,号称“九边”。而山西地区建有“二边”,即大同镇与太原镇(驻守于偏头关)。山西境内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与河北省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等“内三关”,构成了两道拱卫明朝腹地安全的防线。
三、余论
笔者提出的“区位论”,是将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运用于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历史地理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要求研究者细密编织历史演变延续性的同时,全面展现地域间的相关性与差异性。中国历史演变的纷繁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区域社会的反映差异来表现出来,过分笼统地谈论“国家”、“社会”、“历史”等宏观概念,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深入研究与分析这些区域反映差异,会大大加深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而在另一方面,区域历史是整体历史嬗变的一部分,为了更准确理解与分辨这种反映差异,还需要超越单个区域局限的历史的整体观的把握,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时段差异与地域差异,对于区域社会的深入研究同样是大有裨益的。
以山西地区为例,随着历史的变迁,山西地区的政治归属、民族与人口构成以及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在从事区域社会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有个较为清晰的理解,从而为进一步的微观研究提供准确而客观的时空座标。山西区域史之发展,实为中国王朝演变史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就政治区位而言,山西所属东(晋东南)、西(吕梁)、南(河东)、北(雁北)、中(晋中)等五个亚区,都有建立都城的经历,这应该在今天中国境内各省区中是极为少见的。同时在民族发展史上,有不少北方民族部众如匈奴、鲜卑(铁弗)、吐谷浑、契胡、沙陀等等,都是在长期迁居山西后消失的,这对于山西当地的人口构成的影响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山西的各个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构成区域社会的要素都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如果看不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差异,简单将区域社会视为亘古不变的“铁板一块”,那么就很难得出真实可信的研究结论。
本文摘自:安介生著:《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转载自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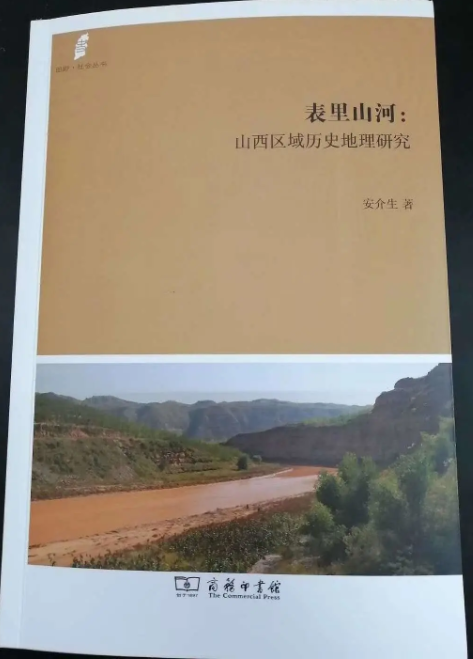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文章转载自:太原道,作者:安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