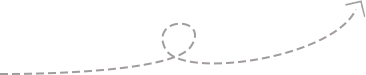彝族的起源——此“夷”非彼夷,此“昆”即彼昆
访问量:243
2024年08月14日 20:51
来源:昆仑谱微信公众号
彝族是我国人口数量排名第六的少数民族,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族群。正因为其古老,彝族的起源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很多研究都不过是脑洞大开的哗众取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老彝文与山东丁公陶文神似”观点。即便个别研究结论已经接近真相——把彝族文字与秦安大地湾刻画符号联系起来。但是其视野、其逻辑、其证据、其推理,让人不得不觉得看起来似乎已经接近真相的结论,只是来自于基于地域自豪感冲动的误打误撞。从彝族分布的空间框架出发,结合其族群历史与现实的历程与特色,彝族的起源并不难揭示。本文要用两个汉字为切入点,彻底解开彝族起源之谜。第一个字是“夷”;第二个字是“昆”。
先来看“夷”字。
2019年,在国内一次高端线上学术对话中,一位国内著名的考古学专家,神乎其神地声称山东丁公陶文可以用彝族的古彝文识读,并现场神奇地将丁公陶文近乎天书般的十一个古文字一字不漏地读了出来。这位专家之所以敢于大胆声称山东丁公陶文与彝族古文字同源,一定是因为他知道:彝族最初并非叫“彝”族,而是叫夷族,是对西南地区多个具有相当共同民族特征性的少数民族的统称。从彝族改为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关心爱护,觉得“夷”字在汉语和日常生活中多少带有贬称之义,遂与彝族代表商量,仔细斟酌,改“夷”为“彝”——取古代宗庙中的祭器“鼎彝”之义。这位专家一定是觉得,既然都被称作夷族,此西南夷族与彼山东夷族一定是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关系极其复杂难以追溯是学界共识,这位专家就没有再对此直觉般的结论做进一步追踪穷究。
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此夷非彼夷”,现代彝族地处西南边境,绝对不会是真正的远古夷族——被称之为东夷的山东古老族群迁徙过来的,这一点在本文明起源系列研究中已经有所阐述:“山东东夷族群也曾经有过向西南迁徙的重大事件,就是4700年前涿鹿之战失败的太皞族,与蚩尤族一道向西南迁徙,在江汉平原停留600年左右,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三苗族群。后在4070年前左右被“禹征三苗”所击败,不得不向更西南方向退却、迁徙,形成了今天的瑶族、苗族和土家族,土家族就是古东夷族的后裔。他们迁徙脚步向西的极限只到达大巴山和武陵山,向南则到达今天的贵州、广西乃至广东境内。历史上东夷族只有这一次大规模向西迁移,沿途和最终都留下浓重的足迹和印记,但没有任何迁徙到达川西横断山脉沟谷盆地的痕迹与记载。而且,按照人类学的规律,站在生存繁衍的轨迹看,极度偏远高寒的川西横断山脉纵切面,对远古先民而言,确乎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龙山文化之后,山东受4200-3900年前大叠灾影响,文明衰落,进入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时代。再往后,山东全境华夏化,原生的东夷族与东进的华夏族完全融合,山东成为华夏族的核心地带,不再被称作东夷。远处意义上的东夷族,不复存在。山东人再往后的大规模迁移,就主要是相对晚近的向正南方向的“衣冠南渡”。
夷族的指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极其漫长而富于变化的历程。
最初的夷族,就是指山东东夷族群,早到大汶口文化存续时期,与中原华夏族,时而对立、对抗,时而联盟、联姻。夷者,“大弓”之人,善射者。此时“夷”字起码是对族群特征的认知识别,即便不是一种赞誉,也绝无后世的贬义。“后羿代夏”是东夷族干过的最为轰动且青史留名的重大事件,事件中射日之说与“大弓”、“善射”内涵高度切合。
往后,中原强盛,周边少数族群广泛出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以黄河中游华夏族聚居地为核心,周边四方以“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并称。镐京之变,西戎在周携王内应之下攻入西周国都是最著名的事件。此时的夷,已经带有一定的贬义。
再往后,夷字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三个字,中原之外的四方族群均被称作夷,即所谓“四夷”,有成语“四夷宾服”。夷字的这个泛指落后地区族群的内涵一直保留并延续至今。
到了秦汉时期,夷字出现了新的内涵,专指西南地区最为边缘最为蛮荒地带的少数民族。以司马迁《史记 西南夷列传》为标志,中原的所有北方族群均称作“胡”,东南方称作“越”,西南方称作“夷”。此西南夷还包含贵州的夜郎国,范围较今天彝族分布地区更大,但是彝族在西南夷中已经处举足轻重的地位。
直到东晋,今四川崇州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西南地区最早的方志(史书)提到夷人之时,已经基本与今天的彝族高度重合了,所以才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的记载和描述。彝族因为古老而人口众多,在早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一枝独秀,最终与西南夷的夷字重合起来,成为了专称。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如白族等,不再被泛称为夷族。
需要特备强调的是,在整个夷字的演变并逐步与彝族关联并最终成为彝族族名的历史进程中,所谓的夷,都是外人,尤其是中原华夏族、汉族对彝族的称呼,而非彝族的自称。彝族自始至终都有自己非常执着、非常高贵的自称——何以“执着”、何以“高贵”,后文将详细揭示。
不过,历史却有非常吊诡的一面,现代彝族被称为夷族的祖先,却有一种特质与真正的山东东夷族高度相似——是不是有因为这种特质而被其他族群误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古老夷族的因素,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现代彝族的神话传说中,有与山东东夷族古老传说高度雷同的桥段——射日。东夷族的后羿射日传说,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流播极广,知名度很高。而彝族在民族史诗《勒俄特依》中也有自己的射日传说。按理说“射日传说”是个性化极强的远古族群神话,两个完全没有发生学共性,相隔数千里的古老族群,要说都衍生出“射日神话”,其概率非常之低。人类那么多族群,除了东夷之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再也没有产生射日神话的了。也许,这两个射日神话,还真有内在的历史渊源,只不过一直没有被大白于天下而已。
来看看山东东夷族群射日神话的起源:中原华夏族自黄帝涿鹿之战一统部落联盟之后,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高阳崇拜,并一直延续到约BC1000年周王朝早期,才因为气候变化,黄淮海大平原形成而式微,被新的国家图腾——龙——带雨生水的农业保护神所替代。黄帝时代与山东东夷族是联盟更联姻的亲密关系,其首领少昊甚至代替黄帝成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从而使得黄帝嫡子昌意、玄嚣错过帝位,只能由黄帝孙辈颛顼登帝位,史称高阳氏。从帝尧开始,华夏族与东夷族关系逐渐恶化,一直到禹孙启子太康,最终失国于东夷首领后羿。华夏族首领是人间圣王“太阳王”,与华夏族对抗并兵戎相见的东夷族首领叫后羿,而后羿射日的传说又广为流传,直至最终演变为神话,合理推论,显然是历史上后羿以射日为政治动员口号来反对华夏族。一遇到大旱年代,农耕为本的中原大地,很容易相信东夷族这个“后羿射日”的宣传口号并为之鼓动,夏代末君夏桀太阳王也一定同此逻辑——“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1”,音犹在耳。
既然彝族并非西迁的山东东夷族群,二者共同拥有射日传说,山东东夷族群射日神话是因为与华夏族因战争而引发的意识形态之争,彝族会不会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远古东夷族和彝族祖先都曾经拥有共同的敌人,以“高阳崇拜”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华夏族。
审视彝族主要生存地带周边最大最好的地段,自然是东北方向,肥沃的成都平原了。成都平原上的远古人群是华夏族吗?当然是!成都平原上文明达到最顶峰时莫过于三星堆,其最具识别度、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器物是牙璋。众所周知,牙璋是石峁和二里头的核心礼器——本《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已经反复交待,那就是夏。所以,三星堆的核心族群自然也一定是夏人族群,同时也自然是黄帝的后裔族群。同时,《华阳国志》记载:“蜀曰邛2”。寥寥三字,揭示出一个古蜀文明的重大秘密——成都平原的主体族群“蜀”,其实来自于川西山麓向阳坡地的“邛”——今天的邛崃、大邑一带。“邛”是一个极其古怪的字,汉字中越是古怪的字,往往越是古老,越是大有来头,因为身份高贵,只能专用。如女娲的“娲”,颛顼的“颛”和“顼”,帝喾的“喾”,因为神圣而孤独。在夏朝灭亡之后,陕北还保留着一个族群,被商人称之为“邛方”,“邛方”就是“工方”,与龙方、鬼方、土方等并称于世,名噪一时。据史载:“工方实乃共工氏后裔”。共工氏拥有一个著名的神话故事:“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3。”尽管共工氏与颛顼帝看起来是敌人,其实是一家人,都是黄帝直系后裔,否则也轮不到他与颛顼争为帝。失意的共工氏与四千年后大明王朝的宁王朱权一系命运极其相似。从共工氏到工方,从工方到邛方,从邛方再到成都平原川西山脉东麓的邛地、临邛、邛州,再到今天的成都市县级行政区划邛崃市,脉络清晰,轨迹分明。可以想象,川西山谷中庞大的彝族,与迁徙到此也兴旺发达起来的共工氏后裔族群,之间发生战争,是高度合乎逻辑的。在遥远的川西,发生了一幕与曾经的山东一样的意识形态斗争故事,面对同样高阳崇拜的黄帝后裔共工氏,彝族先民合乎逻辑地与东夷先民一样发明了“射日神话”——把对方那些自称为人间太阳王的部族领袖射死。
敢于断言彝族射日神话和山东东夷后羿射日远古神话并非同源,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神话,在神话本体上也同样证据确凿:其一,故事的英雄主人公名字不同,东夷曰“后羿”,彝族曰“支格阿鲁”;其二,天上的太阳数量不同,东夷神话中天上太阳有十个,后羿射掉其中九个,留下一个继续发光发热,东升西落,滋养万物。彝族神话中太阳的数量却是六个。两个神话中射日英雄的名字不同还有一点点可能是因为语言流播而讹变,天上太阳数量10个与6个的差别,却绝对不会是流传中发生的错讹,凸显出不同族群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建构出完全不同的远古天文知识体系。
彝族的古称夷族,是他称,即外人对彝族的称呼。中原华夏族因为其著名的射日太阳神话传说,将其与山东东夷族混为一谈,以为他们是一群人。有没有或多或少此种因素,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由此,我们得出关于彝族的第一个结论:此“夷”非彼夷——彝族的夷不是山东东夷的夷。
再来看“昆”字。
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有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2。”从文献上首次把“昆”与今天的彝族联系了起来。此处的夷,就是解放前川西、云南一带的夷族。按照常璩的说法,在夷人族群中,大股的叫“昆”族,小股的叫“叟”族。叟族并不明确指什么,也许是彝族广泛自称“x苏”的苏字的同音。这个昆族与另外一个记载昆明族,就是同一个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昆,明也4。”关于昆明族,司马迁早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记载:“西自同师(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5。”
今天的云南省会昆明,就来自于这个昆明族的族名。汉唐之前,昆明族还多定居在云南西部地区。南诏和大理时期,昆明族因乌蛮和白蛮(可能就是今天的白族)族群的压迫,不得不向东迁移至滇池一带。至宋宝祐年间在此设昆明千户所,昆明作为滇池周边一带广大地域的名称出现并沿用至今。而昆明族这一自西向东迁徙的轨迹,也给追溯其族群起源,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总结从司马迁到常璩再到昆明市得名,现代彝族不应该叫彝族,更不应该叫夷族,彝族有自己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自称——“昆”,按照现代社会民族自决原则,实实在在应该叫“昆族”,或者“昆明族”。
那么,“昆”在彝人语境中是什么意思呢?
在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彝语中,昆发音为“KO”。老彝文中昆是“威望、威严、权威、气概、尊严”的意思。顺理成章,老彝文中“昆”应该就是对部族领袖——称号叫“昆”的王者的崇敬与歌颂——气概威严光明的昆王。段玉裁关于“昆,明也”的阐释与云南老彝文中昆的意思也完全契合。
在本《中华文明起源系列》中,曾经浓墨重彩、连篇累牍地研究和阐释“昆仑”,并彻底解开了位居华夏民族第一神话昆仑之谜。昆仑是用来记录远古人类族群祭祀盛大场景的一个关键词,最终演变衍生为王名,大禹之父鲧和大禹本人字“高密”,都是昆的意思,鲧禹父子是一对“昆”王。鲧建成、禹出生、鲧妻禹母修己西王母统治的石峁古城就是《山海经》记载的昆仑之墟。昆字起源极其古老,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考证它的具体起源年代。唯一可以追溯并确定的是,“昆”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语音阶段,是对祀火崇拜时代对祭祀点火时的拟音以及对圆形祭坛的记形。第二阶段是华夏族进入高阳崇拜时代之后的字形时代,昆仑都有了对应的文字,并且昆字还以鲜明的“日”部彰显其时族群的核心意识形态——高阳崇拜。
昆字的语音和字形演变神话的过程恰好与华夏族远古时代两个重要的阶段相吻合:以祀火崇拜(光明崇拜)为核心意识形态的三皇时代和以高阳崇拜为核心意识形态的五帝时代。三皇中的燧人氏和神农氏都在关中平原,伏羲在陇西河谷高台的秦安大地湾。五帝的活跃空间都在河东盐湖周边一带。
古老彝族先民与华夏族都以昆(或者昆明,或者昆仑)为核心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不同,或王名,或地名、或族名),按照人类学的规律,两个相隔遥远的现代族群,各自独立发展出完全相同且成体系的核心意识形态,可能性微乎其微,二者历史上一定曾经具有高度紧密的相互关系:
1、华夏族是彝族的源头。
2、彝族是华夏族的源头。
3、二者共同拥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
三者必居其一。
逐一分析:
首先,彝族的远古传说中,完全没有中原地区的远古大神盘古、女娲、燧人、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太皞少皞、帝喾、颛顼、大禹等等的只言片语。说明早期彝族与诞生这些英雄人物时代的北方和中原地区并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彝族传说中一定会有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和事迹。就像今天同处西南山区的苗族瑶族,就认蚩尤、盘古为其祖先。傈僳族称自己是颛顼后裔,是追赶太阳的民族(与颛顼族为高阳氏完全契合)。说明彝族并不是由华夏族形成之后从华夏族分离出来的。
其次,按照人类学分布规律,彝族分布北起凉山州,南到红河州的非常偏远的横断山脉河谷盆地之中,连成都平原都不曾有寸土涉足,与传统华夏族聚居之地相距非常遥远且隔着几乎难以跨越的千山万水。从文献记载看其族群的迁徙轨迹是沿着横断山脉的沟谷盆地不断南迁后再偏东迁,没有北迁的任何痕迹。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北方族群不断向南方迁移的历史。所以,彝族也不可能是华夏族的源头。
最后,排除上面两种可能之后,只存在一种可能,彝族与华夏族拥有共同的源头。今天华夏族的主要源头已经基本捋清,起源于陕西甘肃交界处的陇山周边的河谷台地或者黄土台地——秦安大地湾遗址、庆阳南佐遗址,宝鸡周原遗址是真正的华夏族血脉龙兴之地。在三者中,秦安大地湾遗址是最早的文明发生地,是华夏族真正的起源地——传说中伏羲氏的大本营。
彝族会不会就是从陇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源的呢?
可能,非常有可能!
“汉藏同源”是已经被人类学基本认可的理论,而汉藏同源的起点,就是陇原一带。按照汉藏同源理论:早期居处在黄河中游渭河上游的人类族群,一部分向东迁徙,成为汉语语支的主体族群;一部分向南,成为藏缅语支的族群,因为地理分割,形成了众多语族,从彝族分布地带看,已经是与青藏高原最为接近的地理单元了,显然就是这众多语族中的一族。彝族本身就是汉藏同源反映的人类学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的分布位置,在成都平原的西侧,横断山脉之中。大凉山作为彝族的主要分布地域,近300万彝族人口,具有强烈的族群来源指向意义。古人更容易沿着河流迁徙,与中国境内多数河流自西向东流向不同,川西的河流,是自北向南流向。所以,川西横断山脉河谷盆地中的少数民族,南北迁徙多,东西迁徙少。
另外,彝族最具标志性的火把节传统,也从一个侧面对彝族来自于北方陇西作了旁证。华夏族的三皇时代乃至更早,族群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祀火(光明)崇拜,其中秦安大地湾遗址的伏羲位列三皇第二位,大地湾族群很可能有持续的祀火崇拜传统。再者,人类学上,因为北方相对寒冷,南方相对燥热,人类远古时期,南方族群往往更喜欢水,北方族群往往更喜欢火。在彝族分布的同纬度和同海拔地区,其他族群均无火把节传统,唯独彝族有闻名遐迩的火把节传统,显示彝族先民来自北方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我们得出关于彝族的第二个结论:此“昆”即彼昆——彝族的昆与起源于秦安大地湾,早期北方华夏族一直流行作为核心意识形态,乃至经商周两代最终演化为中华民族第一神话的昆(仑),同根同源。
把夷字和昆字导出的两个结论整合到一起,可总结为一句话——此“夷”非彼夷,此“昆”即彼昆。
那么,另外两个高度相关的问题扑面而来:
1、彝族是什么时候从秦安大地湾遗址开始向南迁徙?
2、彝族是沿着什么路线向南迁徙形成现代分布格局?
且听下回分解!
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上,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立即处理删除。】转载请注明:文脉云。